2018年,汕头市南澳渔业码头,岸边摞满了渔民刚刚打捞的渔获,就地形成摊位,卖给前来选购的食店店主。/图 林锐彪
故乡的生活,是一切的原点、故事的开端,是林培源身体里的一部分。他们汇集成了《小镇生活指南》。

林培源刚刚完成了一桩人生大事。
六位中文系教授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在屏幕一端,林培源在另一端——距北京两千公里开外,旧宅二楼,他的婚房。
一个小时后,耗时两年写就的博士毕业论文终告通过,他喜极而泣,走出房间,给刚好上楼的妻子一个长长的拥抱。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将林培源与清华校园、论文资料以及即将圆满结束的博士生涯隔开,将他推回家乡——汕头市澄海区盐鸿镇——一个位于潮州市区、澄海、饶平三地交界,面积约5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仅5万人左右的小镇。这里简单而封闭,却也完好保留着潮汕地区最传统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认同。
此间的生活,是一切的原点、故事的开端,是33岁的林培源身体里的一部分,它们汇集成了林培源的小说新作《小镇生活指南》。
他在出版社制作的推荐视频中说:“我对世界的想象与瞭望,都与潮汕有关。”
小镇异乡人
过去13年,与许多只身远游的潮汕青年一样,林培源每年回家的时间不超过1个月。而这次,他被疫情困在盐鸿足足6个月。
时间骤然放缓,只有身体回了故乡。林培源的心绪还是被外界的变所牵动,回京遥遥无期,论文仍未完成。他形容,自己突然从城市的“侨寓者”,变成了小镇的“异乡人”。
林培源自称有社交洁癖,自小招架不住潮汕繁琐的传统礼数和复杂的人情关系。居家6个月,他只是偶尔与中小学时的老朋友见面,约个宵夜,吃个肠粉,沿着乡里长长的水利渠,一圈一圈地走。他说学业和写作,老同学聊妻儿、新车和周边游。各说各的,也挺开心。
他发现,在老同学的讲述里,身在家乡的幸福,似乎是一件近在咫尺的事情——比如,只消凑一班朋友,把车子开到汕头东海岸高架桥下的大空地,烧烤、聊天、放风筝,很是惬意。
一边是复制父辈生活轨迹的安逸留守,一边是挣脱地理与精神限制的高飞远游。林培源属于后者,但他在这段滞留家乡的时光里,一定程度上理解了同龄人的选择。
在这片背倚莲花山、以水产养殖为主、小而封闭的土地上,林培源是个名人。两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作家、博士等头衔本就罕见,把这些合而为一的,唯独他一人。
母校澄海中学把林培源的照片和作品置入校史馆,历任校长在迎新会上都会提及这位出色的“本校校友”。各路书店老板会托各种关系尝试让林培源帮忙签售,市区各级文联的朋友、周边城市的笔友从不间断。林培源的婚礼当天,他六年级时的班主任搀扶着已经80多岁的、他的学前班语文老师到场——老师们都以教过他这样的学生为荣。
2016年,汕头小公园。这里是汕头老城的核心地域和文化标志。/图 林锐彪
“不知是环境变了,还是自己变了”
伴随路边不间断的摩托车喇叭声、外甥的喧闹和挖掘机的巨大异响,林培源在盐鸿依然坚持每天下午3个小时的工作。汕头市在2020年年初开展雨污分流工程,从市到村,都在凿路。林培源说,村里的工程被私人承包,施工队技术有限,时常会挖开某一户门口化粪池的下水道,两拨人便横着,在路边吵。
老家的房子挨着大马路,隔音不好,楼下车辆路过、行人讲话的声音穿墙而过,打破睡眠。除此之外,隔热也不太好,一到夏天,父母都会搬到相对阴凉的一楼睡觉。为了降温,父亲用上了“土办法”,托邻居买了几块厚厚的泡沫板,铺在林培源房间正对着的楼顶上。
回到这个熟悉又处处局限的地方,林培源除了感叹“以前不知道怎么适应过来的,不知道是环境变了还是自己变了”,只能尽量调节心态,完成博士论文的最后一章。
在此期间,他还收到了各大出版社寄来的超过两百本新书,他一一拆封、码好,为罗伯特·阿尔特的《七个疯子》和比拉·马塔斯的《卡塞尔不欢迎逻辑》两部集子写上书评。
林培源经常想念清华大学博士楼的单人间。那儿有一台代替工夫茶具的美式咖啡机,飘窗上铺着毯子,整齐码放着书。窗外是五道口地铁站。他的博士论文的主要篇章和许多写作都在这里完成,伴着每天有节奏的、列车滑过轨道的响声。
对一个游子来说,13年足够久,久到足以蜕掉一些看似坚固的特质。比如去杜克大学访学时,林培源带了潮汕人标志性的工夫茶具,但妻子不喝茶,他一个人喝也觉得无趣,转而在达勒姆和罗利(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首府)周边寻找地道的咖啡馆,学会了磨咖啡豆,并慢慢依赖上这种新的味道。
于是,盐鸿的老宅里,总有两种香气的交织:父亲照常与来访的朋友冲茶谈天,而林培源更习惯一个人喝网购回来的挂耳咖啡。
父母对林培源颇为开明,但这种开明需要代价——林培源得用足够优秀的成绩,换取人生选择的自由。这是潮汕世俗中不由分说的价值观,是一种不需要摆上台面的潜规则。林培源觉得,父母一直以来不加干涉的表面下,是一种“潜藏的紧张感”。
父亲做过木工,是远近闻名的手艺人。林培源小时候就经常去父亲的工作间拿些边角料鼓捣,小学时用木头做出了一艘带马达的船——他觉得,这种将素材化为成品的尝试很有意义,“我的想象力可能是那时候慢慢培养出来的”。
母亲是一个普通家庭妇女,经常给林培源讲一些当地的民俗风情、家长里短、奇闻轶事。这些零碎的片段,形成了林培源关于潮汕最早的记忆与素材。
母亲几乎没有完整看过林培源的作品。唯独有一次,她偶然翻开了2007年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合集,第一篇是林培源的获奖作品《打马而过的旧时光》,文章写了一些家族旧事,满满堆着母亲初为人妇时的种种难堪与心酸。彼时四下无人,读完这篇文字,她嚎啕大哭。
2013年,汕头市澄海区盐鸿镇。/图 林锐彪
记忆的缝隙与小说的原型
文字和想象力,让林培源与父母、与这片土地和文化达成了某种坚实的连结与沟通。小时候的记忆是最坚固的,它成了持续书写的根基;记忆也是流动的,它成了向外延伸的主轴。林培源从小的见闻,加上好奇心和想象力,构筑了他的小说世界的砖瓦和精魂。
林培源自小记性好,他能记住很久之前与朋友见面的准确时间,以及房间各种摆设的细节。他在初高中时就有意识地训练自己对外界的观察与分析:“比如看到一个东西,就习惯性地在头脑里进行转换,如果我用文字去描述它,我会怎么写?”
《小镇生活指南》中备受好评的《奥黛》,便是在这些传闻的夹缝中流淌出来的。
林培源小学时,听闻乡里有个男人娶了越南老婆、生了孩子。这在当时的盐鸿镇非常罕见。此外,他的一个小学校友的父亲是越战老兵,回乡后从事养殖业,有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一提到越南便格外激动。后来,林培源特地去了一趟广西防城港,每天看戴着斗笠的越南人从边境排队过关,到中国境内打工。
这些细碎的记忆和见闻,化为一短一长两篇小说。林培源先写下《奥黛》,将这些素材进行了融合与想象:一个打过越战的本地男子阿雄想讨个老婆,经一个老人的介绍,娶了越南新娘陈文瑛,短暂地恢复了对生活的知觉与欲望。
但婚后日子不顺,吵闹不断,直到陈文瑛无故消失,阿雄刚刚觉醒的欲望无处可去,生活退回寂寥和一团乱麻的困局,只留下一件泛黄的奥黛,象征着陌生的外来观念冲击和对改变生活的拙劣努力。
《奥黛》中这对仓促结合的异国夫妻一直处于僵硬的对抗状态。文中一句“当年没搞死你们越南人,今日轮到你来搞我”,是林培源对国与国、人与人、历史与现实隐喻的总结,不同文化背景、心态、位置在小小的屋檐下僵持、爆发、复归平静。后来他意犹未尽,将这一题材写成了长篇小说《以父之名》。
作家阿乙如此评价《奥黛》:“林培源写的是现在的事,却似发生在古时或民国。他不是注意去使这个时代区别于其他时代,而是使它消融在漫长时间的湖水中。”
林培源说,讲故事时,自己的声音是被隐藏起来的,如同自己对故乡的观察那样。小说《青梅》中的第一人称叙事,像旁人一样细致而沉静地观察着,用小孩子的眼光安静地看成人世界隐秘的苦难:“我会尽最大努力去削减我作为一个作者的声音,我把对人物的情感、判断甚至道德评判去掉,让叙事人的声音跟角色重合,读者不会被太多观念干扰,整个故事和逻辑会更可信。”
2016年,汕头市南澳岛。/图 林锐彪
潮汕民俗繁多,林培源甚至在小说中虚构或者修改一些民俗,注入他充沛的想象,记录传统的同时破除传统。他在《拐脚喜》中尝试虚构了一个民间仪式——“哪户人家死了人,死者生前穿的鞋就会挂到门前”;《他杀死了鲤鱼》中,虎壁下的方槽本是养龟的,林培源改成养鲤鱼,并在“鲤鱼”这一意象中,寄寓了普通人一辈子生老病死的悲欢。
潮汕民风彪悍,这在林培源记忆里的故乡往事中也得以体现。每当盐鸿镇举办游神赛会,总会有村里的仇家趁着人多打架甚至捅人,各种血腥暴力事件时有发生。这些不断发生的景象,被林培源写进了《他杀死了鲤鱼》中。
比如上世纪90年代末,警察会到村里强行制止游神赛会,反被村民们打得无力还手,纷纷躲到小卖部或者乡间神庙,警车则被村民合力掀翻。村里小孩子骑在大人肩膀上,看村民冲着警察扔石头——一种旧式文化的顽固和难以撼动之处,都在这些飞舞的石块和集体无意识的围观里了。
父子、女性与梦境
父亲(以及父子)、女性和梦境(或曰幻觉),是林培源的潮汕故事中最常见的三个元素。这些反复出现的元素,紧紧交织成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图景。
潜意识里,林培源将父亲的意象跟潮汕的文化环境、社会结构做了同构,“某种程度上,我会把生活的整个环境和背景作为一种强大的父权的象征”,当父亲的意象、父子的互动出现在林培源的小说里,通常代表着一种被动、压抑、走投无路,想用力改变但又无力改变的现实。
而女性则刚好相反。林培源在女性角色的塑造上赋予了更多的自我突围、自我选择的可能,比如《水泥广场》中主动提出离婚的慕云,《姚美丽》中经营电子游戏厅、特立独行的姚美丽。
潮汕传统氛围下的女性,大都饱受压力、依附感强。同时,潮汕家庭的稳固与否与家中女性密切相关。林培源觉得自己的母亲、姐姐和妹妹都是相对独立、有决断力的女性,但这种独立是有限的、被潮汕文化紧紧包裹的。
姚美丽式的独立女性,无论在上世纪90年代还是当下的潮汕乡村都非常少见。她最想倾吐的关于生活的种种,最后只能说给一位虚构的哑巴司机听。
林培源说,“一个女人的秘密只能倾诉给一个哑巴”是一个很偶然的设计,但它却意外地契合潮汕女性“无处可说”的压抑与艰难。
《秋声赋》代表了《小镇生活指南》大多数故事的基本基调:以糟糕的生活为开端,历经过程荒诞的挣扎和努力,依然不见起色。结尾的“他出生的这个家,成了他最后的精神病院”“也只有睡过去时,父母才会觉得阿秋还活着,他们才觉得没有失去他”,写出了潮汕文化中不由分说、压抑沉重的一面。主人公们从绝境走入绝境,从很低走向更低,林培源平静地描绘着绝望的模样,但每个故事的最后,仍然留了一点点转圜余地。
林培源很厌恶在小说里写一个过于绝对的结局,比如让人物死亡。他认为,草率的死亡只能证明作者在偷懒。《小镇生活指南》里,只有《拐脚喜》提及了死亡——一个很潮汕乡间的死法——乡里水沟河道多,下面尽是淤泥,主人公庆喜半夜喝醉栽进去,头先入地,死于窒息。
2013年,汕头市澄海区盐鸿镇。/图 林锐彪
“故乡对他是不设防的”
回想新概念大赛初期,校园文学风靡,少年时的林培源也随了这波风潮,写校园,写青春,加入最世文化,随后的十年(2008—2018),他在签约作家、商业出版和纯文学的矛盾下写作。在不断的尝试中,他终究觉得,城市生活和浮华情感的路数不适合自己,这种被美化过的生活,与出身于十八线小城的自己是格格不入的。
最后林培源决定,他的写作还是得回归这片不完美的、熟悉的、带着温度和记忆的土地,他在《小镇生活指南》的后记中写到,希望用文字构筑一个和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马尔克斯的“马孔多”一样的“原型故乡”,写被生活抛弃的年轻男女、衰老无力的中年男性。这些才是他最熟悉也最擅长的题材。
他回忆起第一个关于潮汕的短篇,叫《春天和一个老人的死去》。文章模仿余华《活着》的叙事,讲了一个老人被儿子儿媳赶出家门,在郊外的草寮中孤独死去的故事。
文学社的老师赞扬了这一尝试,说“你大可以把目光投到你身边,写潮汕的人与事”。2014年7月,《白鸦》发表于《青年文学》杂志;2015年,《邮差》登上《花城》杂志。这是林培源用小说书写潮汕的重要转折点。他很重视纯文学刊物的认可。
2020年,林培源坐在澄海区东里镇与海山镇交界处的堤坝上。/图 林锐彪
新书的书名,颇费了一番心思。《小镇生活指南》是《拐脚喜》的原名,与台湾作家陈雨航在2012年出版的小说集同名。两者有相似之处:陈雨航写的是1960年代台湾东部小镇的生活,林培源写的是由1990年代潮汕小镇生发的悠远幻想。
林培源说,潮汕文学在中国文学史几无地位,甚至整个岭南文学也是如此。他并不讳言自己写作的野心——希望通过自己的叙述,让潮汕文学获得应有的尊重与重视——这也是这部小说集定位成“潮汕故事集”的缘由。
对于“潮汕故事集”的概念,林培源心情复杂。他觉得,一方面小说借此提升了辨识度,被迅速归类到地域文学的框架,迅速激发潮汕读者的情感认同和非潮汕读者的好奇;另一方面也会带来危险与质疑——比如把所有潮汕元素去掉,这些故事还成不成立,能不能打动人心?
他用十篇小说里扎实的叙述、丰沛的情感和融到故事里的小说技艺,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作家辽京读完《小镇生活指南》后评价道:“作者说写小说的要义在于‘不忍’,不忍则意味着‘同情’和‘平视’,在这本书里,作者几乎是隐身的,隐在这些小镇的人物之中,不是岸上观鱼,而是潜入水中,自身也是一条鱼,故乡对他是不设防的。作者从听到的、看到的人和事中间剪取一些侧影,构成一本小镇故事集。在潮汕风俗和当地美食的后面,还有这些平凡而可叹的生活,不仅仅是‘清平镇’,更是所有小镇的微缩模型。”
《小镇生活指南》封面图(中信出版社2020年7月版)
林培源正在准备下一次离开家乡。无论去往何处,他出发的地方,始终不曾改变。
他身上的许多“潮汕性”像老家墙面那样剥落着。但他为潮汕继续书写的意愿,却变得更加强烈。
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上一篇: 搬家是当代都市人最后的体育运动
- 下一篇: 应届生这个身份,才没传说中那么吃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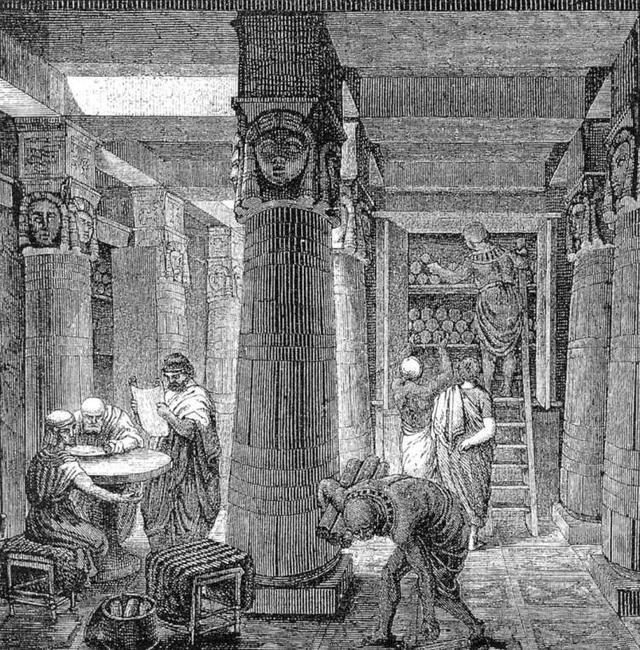

最新留言
说:写得非常好!
2020-10-28 11:1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