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苏枫
与外界对“山东大汉”管谟业(莫言本名)的想象不同,65岁的莫言,中等身材,身高1.72米,体重75公斤,微微发福。
莫言说,别人看《红高粱》,都想象他一定是两道剑眉、双目炯炯、人高马大、声若洪钟,动不动就跟人打架。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好多人说,你怎么可能是莫言?你冒充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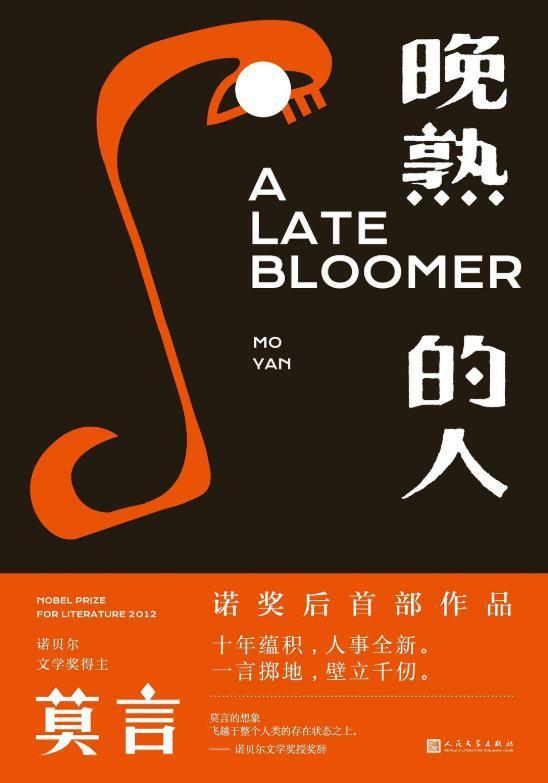
不过,莫言认为这是一个好作家的标志,“作家的作品跟他本人的反差越大,说明这个作家的创造力越强”。
不少作家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都会陷入所谓“诺奖魔咒”,持续写作变得困难。
莫言认为,所谓“魔咒”,也许是个客观存在。获奖之后,莫言曾被俗事缠身,举笔维艰:“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时,一般年龄都比较大了,创作力减退,再加上获奖后社会活动和各种应酬增多、成名之后的心理压力,都会影响创作。但也有很多作家获奖后写出了重要作品。”
时隔8年,莫言出版获得诺奖之后的第一部作品《晚熟的人》。
《晚熟的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莫言说,获得诺奖后,自己从“讲故事的人”成了“被讲述的人”。“从讲故事的人变成故事中的人,这是一个崭新的角度,这部《晚熟的人》,基本建立在这个新的角度上。”
“小说中的莫言,实际上是我的分身,
就像孙猴子拔下的一根毫毛”
《晚熟的人》共12个故事,其中有4个故事是今年春天在故乡高密写的。
莫言说:“这些小说是我的创作风格的延续,但又明显注入了新的元素。如果说我过去的小说里有很多剑拔弩张的东西,这一批小说里,更多的是心平气和。小说中的人物,既有我过去小说中人物的血缘承继,又具有了明显的时代特征。”
莫言在第11个故事《红唇绿嘴》中写道:“互联网时代,大部分农民也都成了智能手机的使用者,他们几乎无师自通地成了网络大海里的游鱼。他们使用着网络,也创造着网络,他们像鱼虾一样在网络海洋里寻找着自己的食物,有时候也能扑腾出大大小小的浪花……”
“新人”高参是莫言塑造的一个小人物,此人拥有五部手机,开了两个公众号,靠贩卖谣言发家致富。她给故事中的莫言“上课”:“我们要做网络的主人,不做网络的奴隶。网络是天堂,网络也是地狱;可以利用网络伸张正义,也可以利用网络冤杀好人;可以利用网络消费,也可以利用网络赚钱……”
莫言对此的诠释是:“高参这个人物是饱经苦难的,但这些苦难并没使她变得崇高和善良,而是使她变成一个不受道德约束的逐利者。这样的人在当今社会中并不少见,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在自己的圈子里找到这样的人。提防这样的人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要防止自己变成这样的人。”
将“莫言”放进文本的游戏,莫言早在小说《酒国》《生死疲劳》中就已试过。《晚熟的人》中,第六个故事《诗人金希普》和第七个故事《表弟宁赛叶》刻画了两个假诗人,一个利用一切机会自我包装、炒作甚至欺诈;另一个则打着文学的旗号做了半生的荒唐事,自认奇才,长于混圈,活在幻梦之中,其原型是莫言村里的人。
《晚熟的人》呈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高密东北乡,反映了中国近年来城乡高速发展的形势,故乡的人和事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电视剧《红高粱》的取景地就在莫言老家高密。/视频截图
莫言说,自己会努力凭借“高密东北乡”这个开放的概念,通过创作使之成为中国的缩影,努力使那里的痛苦和欢乐与全人类的痛苦和欢乐保持一致。
莫言描绘了形形色色的众生相,他们来自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拥有千奇百态的人生经历。这些人和事过于真实,仿佛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莫言说:“《晚熟的人》由于使用了第一人称写作,读起来会给人一种仿佛我写的都是真人实事的感觉,这正是我追求的艺术效果。但实际上,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大部分是虚构的,即便有些人物原型和故事原型,那也是做了大量的艺术加工的。文学艺术中所包含的对现实的超越和对未来的朦胧指向,更是得自作家自身的敏感和预感。”
“小说中的莫言,实际上是我的分身,就像孙猴子拔下的一根毫毛。他执行着我的指令,但并不能自己做出什么决定,我在观察、记录着这个分身与人物交往的过程。”莫言说。
莫言的书法也充满了“戏谑”的情趣。
这本书以“晚熟的人”为名——“晚熟”是莫言故乡的朋友们挂在嘴边的戏谑之词。莫言认为:“这里大概有两层意思,一是因为各种原因,有的人心智开启较晚,或者没有表现才能的机会,而一旦机会来临,他的智力突然大增,才能也显示出来,这就是所谓大器晚成;一种是因为各种原因,在前半生装疯卖傻、隐藏锋芒,借以保护自己——当然也有人在装疯卖傻中体验到了奇特的乐趣。而到了后半生他突然正常了,大放异彩,才华横溢,令人刮目相看。小说中的蒋二,应该属于第二类。根据我的经验,生活中有一些人,说自己傻,夸别人聪明,这样的人其实是人精。而有一些人看似聪明,也自认为很聪明,天天骂别人是傻瓜,但其实他才是傻瓜。”
“千万不要惊动地方政府,
给人家添麻烦”
获奖8年来,莫言一直在创作,或者在为创作做准备。他写过戏曲、诗歌、小说,也到过很多地方旅行和考察。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你所做的事,都有可能成为小说的素材或灵感的触发点。”
莫言一直都是“吃得了大苦”的作家。2020年大半年,莫言和夫人住在高密的南山,此处茂林修竹,松树繁盛。因为疫情,他蛰伏半年。从6月16日到8月23日,在庚子年的三伏天,山东最热的时节,莫言以胶东半岛为核心,行走了诸城、胶州、青州、安丘、潍坊、莒县、五莲、邹平、莱州、即墨、平度等23个县市,行程近万里路。
他此行的目的是搜集相关资料,研究地方文化,为新作蓄积能量。
这个团队的构成很简单,一行三人,莫言、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以及一个朋友借给莫言的司机师傅。行程安排得非常紧凑,早出晚归,披星戴月——他们一般是早晨7点30分前后从高密南山出发,夜里10点前后回家。
乡村生活对于莫言来说,属于“故乡的文学”。/资料图片
作为莫言的助手,毛维杰曾与莫言商量,是否提前与地方文化部门联系,以便参观博物馆等场所。莫言说:“千万不要惊动地方政府,给人家添麻烦。”
年过花甲的莫言,在三伏天持续奔波,精神状态极好。他午休时间在博物馆附近的小饭馆吃个工作餐,趴在饭桌上打个盹,下午继续工作。
离开饭馆之前,莫言习惯说:“今天中午我买单,让我享受一下请客的乐趣。”
下午考察结束,莫言一行一般都是连夜赶回高密,有时候实在太晚了,莫言会邀请毛维杰一起在家喝点酒。两人边喝边聊家乡的变化,聊文坛趣事,聊书法鉴赏,聊创作计划,聊今年的农事、今年的雨水。
莫言是个懂酒之人。他考察过很多酿酒厂和酒博物馆——安丘市景芝酒文化博物馆、即墨老酒博物馆、青岛啤酒博物馆、烟台张裕酒文化博物馆等。每到一个酒厂或酒博物馆,莫言都要品鉴一下,剩余的酒,倒在手心里,两手摩擦,深呼吸,说出酒的品格。
莫言说过:“人生最痛苦的事就是面对镜头说话,最幸福的事是在酒庄喝酒。”
在毛维杰的印象中,莫言是个喝酒“有数的人”,很少喝醉。“他是个平易近人的邻居大哥,又是一个风趣幽默的智者。他能居庙堂之高远,又可安乡野之僻壤。他是一个心地善良、有怜悯心的人。”
电影《红高粱》里,就埋着莫言对酒文化的敬意。/视频截图
作为一个“老百姓”“普通参观者”,莫言在两个月内“偷偷”去了诸城三次,那里,是苏东坡当年为官的地方。
在诸城博物馆一楼大厅刷身份证排队入场的时候,戴着口罩的莫言被讲解员认出来了,迅速报告领导。还没等领导出现,莫言赶紧“溜”了——“千万不能被当地政府发现”,这是他获奖之后的一贯作风,他认为,这个社会是一个巨大“名利场”,“要警惕名利对人的牵制和伤害”。
老家的村民都在传,莫言当上了“好像是什么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但莫言的生命重心一直是作品。
老父亲对莫言的告诫是:“获奖之前与别人平起平坐,获奖之后要比别人矮半头。”
纪录片导演张同道为了拍摄《文学的故乡》,前前后后与莫言打了三年交道。
莫言说,“要警惕名利对人的牵制和伤害”。
莫言把自己放得很低,推辞说“我有什么好拍的”。张同道说:“您的价值比您预想的可能要大。”
张同道执着地一次又一次地去跟莫言谈。甚至未经莫言同意,张同道就先跑到山东把高粱地拍了,因为高粱不等人,再不拍高粱就收了。
张同道说:“本来,莫言老师觉得在摄影机面前很难受,后来他可能觉得我这个家伙太难缠了,心想要么就让我拍一回吧,打发了事。他小说里有沼泽地、海洋、大河、大川,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场景都有,但你到高密去看,一马平川,有些河也早干了。是他那支神奇的笔,让这块土地生出了翅膀,生出了灿烂的、礼花一样的风景。”
只要人存在、语言存在,文学就存在
高密人“小廖”是《晚熟的人》里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毛维杰。
毛维杰多次见证了日常生活进入作家笔下的过程——那是2011年12月,毛维杰给返乡过年的莫言当司机兼秘书。他们一起去大澡堂洗澡。
其间莫言遇见了在棉花加工厂工作时的工友,几个人在水池里寒暄了一阵,此事便过去了。
不久后,毛维杰发现自己成了《晚熟的人》第九个故事《澡堂与红床》中的人物,那小县城的澡堂变成了热闹的文学场景。
澡堂文化与现代人生活渐行渐远,反倒增加了它的戏剧性。/《洗澡》视频截图
莫言文学馆于2008年11月竣工并正式开放。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奖当晚,文学馆灯火通明。中外160多家媒体云集,聚焦在这里,传播着激动人心的消息。门前车来人往那个盛大的场面令毛维杰记忆深刻。
莫言文学馆创建已有12个年头,原是以一幢旧楼改造而成。今年当地政府着手在高密东北乡建设新馆,那是一座四层建筑,目前完成了两层。
同时,当地政府正在打造高密东北乡诺贝尔雕塑公园,准备在户外设立包括莫言在内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们的雕塑,以提升当地文化形象。
毛维杰以高密政协委员的身份给政府提出建议:“六点一线”(六点:莫言祖居、莫言文学馆、莫言文学馆旧址、莫言南关旧居、莫言小区——翰林院、莫言南山居),构建莫言文学场馆整体格局,打造高密红高粱文化艺术品牌。这一建议得到了高密有关部门的答复。
毛维杰第一次见到莫言是1985年冬天。他读了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同事告诉他,那个作者是她小学同学管谟业,管家就在校门口胡同东侧。
管谟业当中的“谟”字不就是“莫言”吗?当时的莫言30岁,是个健谈的青年。他引用了海明威的一句话:“童年的苦难是作家的摇篮。”他还说,“好的小说就是揭示社会生活底层、那些人性的扭曲的东西”。
很难说是社会造就底层,还是底层人成就了社会,《红高粱》就是一个例子。
毛维杰最近一次见到莫言是2020年9月14日上午9点30分,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大门口。
获得诺奖之后,来自全球各地的出版社、杂志、报纸、文学爱好者给莫言寄来了大量文学作品,有希望被推荐的,有求签名的……莫言把自己在北京的家、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中国艺术研究院三个地点的书刊汇总装箱,共计74箱书刊,捐赠给莫言文学馆。
盛名带来流量,流量带来重负,莫言消解的方法是“返乡”。
“流量”是莫言少年时期就很熟悉的词:“那时候每到暑期,我家房后那条河的水库就会开闸泄洪,水利部门会向下游通报,将有多少流量通过。流量越大,危险越大,所以,我对这个词有恐怖感。互联网上的流量当然与河道中的流量不能画等号,但是不是太大了也会造成某种危害?我不敢断言。但我猜想,就像洪水流量冲不走河中的礁石一样,网络上的流量也冲不走文学。因为文学是关于人的学问,是关于语言的艺术,只要人存在、语言存在,文学就存在。至于文学在流量时代的作用,跟文学在任何时代的作用是一样的,文学不会依附流量而存在。”
莫言说:“最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之大,可以用天翻地覆形容。城市如此,农村更是如此,我过去小说中的高密东北乡,在现实生活中已找不到踪影,但它并没有消逝,它存在于记忆中,存在于语言中,也存在于许多事物的内核里。将逝去的留不住,要到来的也拦不住。旧的东西总会留下痕迹,新的事物里总是有旧事物的影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上一篇: 崛起的1.6亿00后,比你拼多了
- 下一篇: 传销解救师:我们的目标是早日失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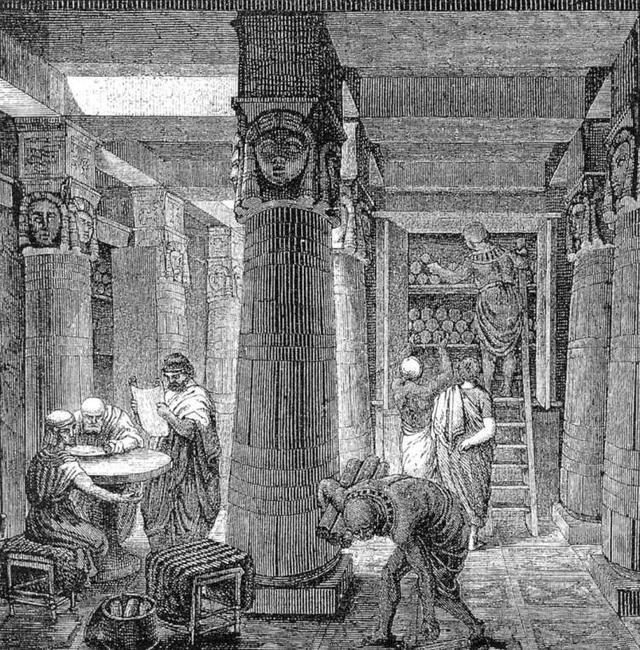

最新留言
说:写得非常好!
2020-10-28 11:1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