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刘旭
作家止庵。/受访者供图
止庵的前40年,是在奔忙中度过的。1970年代末他开始在报刊发表作品。为了生计,1990年代他先后在两家外企负责推销医疗和通讯的设备。他竭力工作的原因很纯粹,为了能早点“退休”,过“闲人”的日子。2000年年初,他如愿了。当同辈人迫切地寻求财富和社会地位时,他则搬离闹市区,过起一种缓慢而闲适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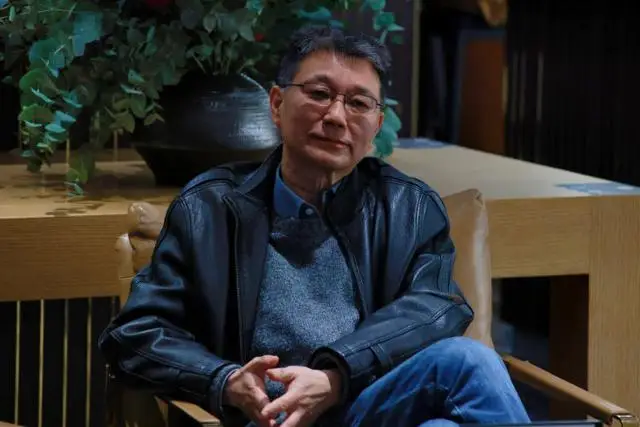
这种不疾不徐贯穿了止庵后续的阅读与创作。他研读周作人、《庄子》和张爱玲,编著了数本相关的书籍。在一些文化活动上,也总能见到他的身影。60岁这年,他酝酿了二十几年的长篇小说《受命》出版了。
“《受命》写了一个新人与旧人并存的时代。”
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止庵就曾写过不少小说,但在他看来,当时的小短篇都是练笔而已。1988年,他由一个观念出发,构思起了自己的长篇小说。那时他正在读《史记》《东周列国志》等作品,他对书中伍子胥的故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想,能不能写一个类似的复仇却没有成功的故事呢?渐渐地,他的脑海里开始有了雏形,而后的两年时间,他写完了人物小传。
小说的男主角被他设定为一个名叫陆冰锋的口腔科大夫。之所以选择这个职业,与止庵早期在口腔科的工作有所关联。写的过程中,他能清晰地知道人物在什么时间点应该去做什么事。除此之外,他觉得这也便于推动后续的情节发展。正是有了这个职业背景,冰锋才能一步步地接近最后的目标。
故事里,冰锋的父亲因人生的种种不顺遂,在地下室自尽身亡。多年后,母亲才告诉冰锋,令其父亲陷入绝望处境的是一个名叫祝国英的人。冰锋依循着父亲在《史记》书页中留下的遗言,开启了一场复仇之旅。而这个寻仇的历程,与止庵喜欢的伍子胥的故事也达成了某种程度的互文。
电视剧《斯巴达克斯:复仇》剧照。
写完小传,止庵因为忙于外企的工作,写作也就被搁置了,一放就是1/4个世纪。2016年,他找出了旧时写的日记,将相关内容誊抄下来,重新构思,最后形成了如今的这个文本。在书的首页,他引用了《庄子·人间世》中的“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在止庵看来,句子中所体现的命运感同样适用于他的男主人公。
止庵说:“渴望复仇的冰锋是一个活在过去的人,他身上背负了太多旧的包袱,他不关注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也不太愿意走入新的时代。”所以,在小说中,止庵没有选择全知视角,而是采取了有限的第三人称视角来书写。
这种技巧,是止庵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所习得的。选择这样的方式,也就意味着除了主人公之外,所有的人都变成了客体,而这些客体的命运走向,也就具备了更强的不可知性。止庵巧妙地利用了该视角的局限性,通过对视阈的框定,在文本中再造了一个空间,读者对其他角色的感知,其实都是源自于冰锋。
有些朋友在读过《受命》之后,直白地同止庵讲,并不喜欢冰锋。止庵觉得,他很能理解这些想法,“因为冰锋是一个被动、消极且不成事儿的人,对待任何事情,他都太过有原则,这种类似‘心理洁癖’的道德观,是当代人所没有的,因此他不被认可,也并不意外”。
反而是书中的两个女性角色让读者们很是喜欢,这是止庵先前没有预料到的。在小说里,“仇人”的女儿叶生是个典型的文艺青年形象。她与冰锋一同参加诗会,看外国电影、话剧与展览。而同事芸芸则与文艺并不沾边儿,但她专注于生活本身,并且能够敏锐地发掘社会的变化。
郝蕾在电视剧《情满四合院》中。/《情满四合院》剧照
书中借冰锋的口,如是写道:“但她(叶生)只是对自己从未接触过的生活感到好奇,尽管真诚,毕竟像是闹着玩;芸芸则是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未必有多大乐趣,但确实担得起一个家来。”两个人都呈现出了各自身上独有的特质。用止庵自己的话说,“她们未必完美,但都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在塑造她们的过程中,止庵对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也有了新的体悟。他说:“坦率地讲,我现在已经不觉得文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了,文艺并不坏,它只是万千活法中的一种。”在书写时,止庵就完全摒弃了对文青仰视的那种态度,他希望能尽量地落实一点。在他看来,《受命》这部作品,从根本上来说,是在写一个新人与旧人并存的时代。“社会在分层,他们都在改变,很多冲突也就由此产生了。”
“我想力所能及地去再现八十年代。”
为了完成《受命》,止庵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希望自己写出来的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部能如实反映时代风貌的作品。
由于故事发生在1984—1986年间,所以止庵特意翻看了这个时间段的报纸。他一早就去图书馆里,泡杯茶,一直待到很晚。他试图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精品购物指南》等刊物中找当时最真实的生活印记。他一边阅读,一边筛选,“鼓楼拆迁”“首都电影院改成立体声”,这些看似零碎但很珍贵的生活细节都被他记录了下来。等他将材料打印出来,发现居然有700多张。
那些来自旧时的讯息,有的变成了小说角色的谈吐,有的则直接进入了情景之中。譬如,在主角冰锋去医院找祝部长复仇的那天,他的弟弟铁锋便给他打电话让他帮着去买体育彩票。体彩开售的事情,止庵只是隐约地记得,他问了经历过的朋友,但朋友们也描述得不够精准。这样的情况下,报纸就成了他追寻过去线索的一种方式。
报纸和社交媒体成为了止庵追寻过去线索的方式。/Pexels
社交媒体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止庵在20世纪80年代曾做过一段时间记者,当时事务并不繁重,因此那也成了他与生活贴得最近的日子。那段时间里,大多数他行走过的地方,他都保有记忆。但有一些,随着时间的久远,也渐渐模糊了。
为了写得准确,他把自己需要的“记忆碎片”发布在微博上:“新街口丁字路口西北角把角的,是副食品商店还是菜市场?”“(19)85年的时候,北京到天津车票是多少钱?”在他发布不久,就有人私信他,老照片、汽车时刻表,都成了他回溯过去的介质。
诸如此类的事情比比皆是。在外人看来,虚构作品在这些事物上本不必深究,但于止庵而言,他必须这样做。他说,如果这部作品是20世纪80年代写下来的,那这些可能并不重要,因为它正在身旁发生。他说:“恰恰是因为隔了几十年,当那些地点、事件都成了历史,趋近于消失时,这些也就有了意义。”
在书中,止庵还用大量的笔墨书写了花草、饮食与服饰。他认为,人物和故事是“骨架”,而这些生活里的细枝末节则是小说的“肉”。他说:“现在的读者看惯了进度快的小说,却忘记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本来是挺慢的。”那些在当代人视野里被忽视掉的风物,止庵要将其重新捡拾起来。
“植物是世界上唯一不变的东西”,他观察周边的花草树木,写了一整年的日记。迎春、玉兰、杏花、桃花等,他都能清晰地说出花期。而这些能反映时令的东西,也被他安放在了故事当中:路边国槐的香气能引起冰锋对一篇小说的联想;而月季、串红、矮牵牛的花丛里,诗歌小组的周末聚会也正在发生。
“月季、串红、矮牵牛的花丛里,诗歌小组的周末聚会也正在发生。”/Pexels
除了这些,止庵还把那个时代人的基本精神状态做了一番描摹。譬如,在书中,他这样写道:“祝部长抽出一支烟,点燃之际吸了一口,但马上就吐了出来。他举着之间夹住烟卷的那只手,偶尔用另一只手将飘散的烟赶向自己,鼻子深吸一下,看上去特别享受。”止庵说,“二手烟”的概念是后来才进入国内的,这是八十年代的人独有的动作,“我不止一次亲眼看见别人是这么抽烟的”。
止庵说,这些不写也完全可以,但他还是“想力所能及地去再现八十年代”。于他而言,那个记忆里的八十年代并不像文艺作品中的那么美好。他觉得,当时精神世界的东西诱惑很多,但物质层面人们却又感觉到窘迫。对于无法改变现状的人们来说,没有出路其实是挺痛苦的一件事。
“写一本真正以城市为主体的文学”
在当代文学的书写对象当中,乡土往往是更受关注的。偏远的地带、边缘的人物,都成了极为出色的文学素材。对于城市的叙事,相比之下则是略有缺失的。大多提及城市的文学,其角色也往往是作为对抗性的存在。止庵就读过很多这样的书,“主角可能是农民,之后会写进入城市的种种不习惯”。止庵不想再去那样书写,他希望能以城市为主体,写一写本身就生活在这里的人。
于是,止庵把故事的地点放在了最为熟悉的北京。而人物,他不选择那些达官显贵,也不去着重描写底层。他觉得前者是官场小说的使命,而后者,也有其他的一些作家在发掘。他单纯地想在有限的篇幅里,写一些生活有层次、有质感的平民。
止庵说,他小说里的人,有稳定的工作,都是这个城市里的一分子,但在时代的大潮下,他们又都发生了位移。“这群脚踏实地的生活者,本身就是值得书写的。”止庵认为,描写城市中间的这部分人,并不需要太多的戏剧化事件。
止庵认为,描写城市中间的这部分人,不需要太多的戏剧化事件。/《情满四合院》剧照
止庵提到了《红楼梦》《半生缘》等小说。他说,这也是他作为创作者的一个尝试,他希望能像这些优秀的作品一样,用最简素、最平实的生活,来建构起人物关系,不需要轰轰烈烈的事情,就能捕捉到这群人心理上或者意愿上的变化。在他看来,真正优秀的城市小说应当像詹姆斯·乔伊斯所著的《尤利西斯》那样:“主人公和都柏林这座城市是实时发生互动的,城市在文本中要发挥很大的作用。”
在《受命》当中,不乏类似的例子:新年之夜,在西长安街上的花墙底下,冰锋与叶生发生了一次交谈。止庵说,这次交谈的很多内容只能发生在当时的北京,如果换成上海,或者将时间调整为1980年代末,就没有那个味道了。在他的理解中,城市文学的意涵很深刻:“它不仅提供了一个氛围,在那个环境当中,城市生活应当进入到人物的种种经历里。”
从文学“鼎盛时代”走过来的止庵,深知如今小说的影响力已经不再像从前那么巨大了。但他知道,有太多微妙的东西,是短信息和表情包无法承载的。他坚持要以这样的方式完成《受命》,是因为他始终相信,文学需要留下那些缺失的印记。他说:“文学其实表达不出太多的复杂性,它只能传递一部分。但是如果连这一部分也丢掉,那咱们就都彻底变成简单的人了。”
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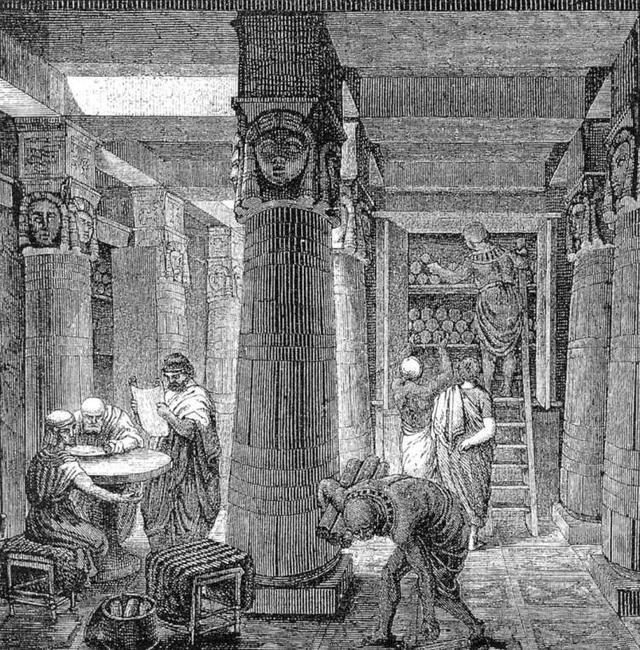

最新留言
说:写得非常好!
2020-10-28 11:1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