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姆不仅写过好几部东方游记,还写过以东方为背景的短篇和长篇小说。1919年9月,毛姆第一次到中国各地游历,1920年初访问香港。第二次来中国是在1922至1923年间。他为此搜集的素材,先后出现在剧作《苏伊士之东》(1922)、游记《在中国屏风上》(1922)、长篇小说《面纱》(1925)和《偏僻的角落》(1932),以及众多的短篇小说里面。
他对中国人的语言、戏剧和宗教信仰完全没有兴趣,却格外关注来华传教、从政或经商的英国人。这样一来,无论是他在游记还是虚构故事里刻画的中国人,无论是在《苏伊士之东》的北京,“全世界最适合度过余生的地方之一”,还是在《面纱》里的香港,无论年龄性别和职业,无论有名无名,他们往往都只是身份游移、面貌模糊的过场点缀。
例如,《苏伊士之东》虽然以北京为背景,但女主角却是嫁给了英美烟草公司驻北京办事处雇员的欧亚混血戴茜·安德森。她的恋爱对象是英国公务员,卷入三角恋的另一位中国富商李泰诚则是爱丁堡大学的毕业生,喜欢的诗人是罗伯特·彭斯。这样一来,毛姆就巧妙避开了自己并不熟悉的中国本土人物形象塑造问题。
《面纱》的译者张和认为,“毛姆以殖民地时期的香港与中国内地某城市为故事背景,让西方读者体验到了来自东方的‘异国情调’。”
他描绘了“瘟疫肆虐的中国城市、脏乱差的中国街道、意味深长的中国牌坊,以及瘆人的中国棺材,勾勒了中国用人、厨子、乞丐、弃婴、苦力、军官、士兵、官员、小脚老太、古董店老板各色人等的画像。毛姆笔下的中国或中国人,既是写实的,也是想象的。而海关官员维丁顿与‘满族公主’的爱情故事则更多带有猎奇乃至虚幻的成分。”但他认为毛姆并不完全是东方主义的视角。
“叙述者说:‘此前,凯蒂耳中所听到的中国,尽是什么颓废堕落啊,肮脏不堪啊,还有糟糕得难以言表啊。眼下却是她重新认识中国的好时机,仿佛遮蔽中国的一道帷幕被迅速掀起了一角,她在飞快的一瞥中,窥见了一个丰富多彩、意味隽永的世界——这是她在梦中都没见过的世界。’在这里,‘帷幕’被赋予了跨文化认知的主题内涵。”这里的“帷幕”,就是小说标题里的Veil。这个名称的直接来源,是雪莱的十四行诗《不要揭开这彩绘的面纱》(Lift Not the Painted Veil,1818)。主题关联更密切的典故,则是雪莱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Unbound,1820)第三幕第三场,大地对亚细亚的死亡之问回答道:“死亡是一道面纱,活着的人都称它为生命/他们睡去,面纱被揭开了。”
[英]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 唐建清 / 上海译文出版社
平心而论,毛姆从来不曾深入了解到中国文化的内核,这主要还是他个人兴趣缺乏的缘故,此外,他也怀疑自己能否摆脱当时普遍的东方主义思维模式影响。1921年,他给英国驻华使馆的二等秘书、著名的东方学家H. I. 哈定写信,请他帮忙审阅以中国之行为素材的三部作品。哈丁提出了几项意见:
1. 毒死自己讨厌的亲戚,这种现象在中国不比在英国更常见,所以不能用“惯常”(familiar)这个词来形容;
2.“奇特”(singular)的用法也不好。虽然中国人可能让英国人“觉得奇特、古怪、滑稽、稀罕、陌生、神秘等等,但与此同时,我们给没有交往经验的中国人留下的印象也一样”。毛姆虚心接受意见,但是关于第二条,他说这可能是误解:“我说中国人奇特,原因并非他们是中国人,而是因为他们明显有别于其他民族的艺术才能。”
《在中国的屏风上》有一篇名为“哲学家”,是毛姆与辜鸿铭见面时的交流记录。它属于国内研究者谈论最多的篇目,为我们提供了毛姆对中国文人情趣和艺术本质复杂性的直观看法。至于毛姆的记叙是否完全真实可靠,香港学者宋淇提供过另外的资料佐证,将毛姆与他的父亲剧作家宋春舫见面的细节进行对照比较。
毛姆无法确信自己能否真正把握仓促印象里的中国精神,就像他无法想象辜鸿铭近乎恶作剧地给他题辞赠字,等他回英国后专门请人解释,发现它竟然是青楼欢场的艳情诗歌。《在中国的屏风上》第五十五章结束时对某个西方汉学家的批评,表达了毛姆对中西跨文化理解的深刻疑虑:“然而这是一种专家式的生活。艺术和美似乎并未触动他,当我听他饱含共情地谈论中国诗人时,忍不住暗自怀疑那些最好的东西是否最终都从他指缝间滑落。这个人仅只是通过字纸书页触碰真实。可爱的莲花只有庄严神圣地载入李白的诗句,他才会感动于它的悲怆华彩;娴雅的中国姑娘发出笑声,只有通过精雕细琢的完美呈现,才能让他的血液奔涌。”
除了到中国以外,1916年毛姆就和哈克斯顿一起从旧金山出发,经夏威夷、萨摩亚,向南至斐济、汤加和新西兰,随后向北到塔希提,最后回加利福尼亚。1921年毛姆以这一次远游南太平洋地区的经历为背景,出版短篇小说集《一片树叶的颤动》。
同年,他在哈克斯顿的陪伴下前往新加坡,再到达英属北婆罗州。途中穿越河流、村庄和丛林小道,还跟成邦江监牢里的一群押解囚犯同舟共济。这段经历里的故事场景和人物形象,在他第三部短篇小说集《木麻黄树》(1926)里反复出现。尤其是在《赴宴之前》《驻地分署》和《胆怯》这三则短篇,都有浓墨重彩的描述。这部作品刻画的诸多真实细节,让他的文字与马来亚的形象建立了类似于吉卜林与印度之间的联系。
但是他对素材人物的过度发掘,尤其是各种酗酒、通奸与人格道德缺陷的描绘,导致许多当地的殖民人士与他断绝往来。毛姆后来在《木麻黄树》的美国版后记里狠狠挖苦了这些人的品味见识:“就算去了东方,他们的生活环境依然与小市镇一样狭隘,他们身上具有种种小市镇的毛病缺点,而且似乎特别喜欢寻找作者笔下人物的原型,尤其是刻薄、愚蠢、罪恶的人物。他们不了解文艺,不明白短篇小说角色的性格外貌是由情节需要决定的。”
[英]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 黄福海 /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22年,毛姆再次前往缅甸,途经仰光、曼德勒、萨尔温江(怒江),骑着骡子来到东北部掸邦地区的景栋。随后前往曼谷,坐船去柬埔寨,徒步到吴哥,再乘船到西贡,沿着海岸线从顺化驶向河内,辗转在1923年4月来到香港,横渡太平洋到达美国,然后回伦敦。七年过后,他把这段经历写入《客厅里的绅士》(1930)。1925年他再次前往马来亚,并以此为素材完成了短篇小说集《阿金》(1933)。1934年他出版《东方与西方》,继续冷峻而无情地刻画西方殖民者在海外肆意妄为、无从皈依的迷乱生活。他在1932年出版《偏僻的角落》,以马来地区的荷属东印度群岛为主要背景,黑斯廷斯认为它“充满了浓厚的神秘色彩,包含所有让人喜闻乐道的元素:肉欲、罪恶和幻灭;它明显受到康拉德的影响,犬儒而机智,在毛姆所有的长篇小说里,它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最强烈。简洁而克制的笔法,勾勒出一系列的难忘印象:炎热、各种声音、污秽,以及热带葱郁而神圣的美感。”
《客厅里的绅士》记述了毛姆的一段感慨:“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几条大河,布拉马普特河,伊洛瓦底江,萨尔温江,湄公河,沿着平行水道奔涌向南,滔滔江水一路注入印度洋。颇为无知的我到了缅甸才听说萨尔温江,而即使那时它对我而言也只是一个名字。它完全没有恒河、台伯河、瓜多基维河那样能够引发联想。只是在我沿江而行,它才对我产生意义,某种意味深长的神秘。”无论是中国还是缅甸,吴哥还是景栋,伊洛瓦底还是萨尔温江,毛姆的亚洲之旅,更多追求一种时代在场感,以浸入式的异域文化体验而获得自我更新。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他冷静细致的记述,即便带着浓厚的文化滤镜,仍然反映了东方的部分真实社会状况,西方政治经济入侵带来的剥削、压迫和侵蚀,西方殖民者的自我封闭与适应,东西方文化在正负两方面的交互影响。
[英]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 周成林 / 上海译文出版社
除了记述与虚构之外,在纷乱的时代背景下,毛姆还想从遥远的东方寻找到精神自由和安宁之道。他在《月亮与六便士》里将个性解放的希望寄托于纯粹的艺术追求,以及塔希提岛代表的原始本能。二战过后,他受衣修伍德等人影响,又试图从东方宗教智慧,尤其是印度的婆罗门教寻求答案。但他同样由于缺乏持续兴趣和深入了解,所以最终仅流于浅层想象,或者停留在似是而非的神秘主义层面。
研究者经常用毛姆的短篇名作《雨》,来分析他对基督教虚伪伦理的抨击。确实,性与爱情的主题,是毛姆揶揄和瓦解教条的利器。《月亮与六便士》结尾里说:“我的亨利叔叔在威特斯台柏尔教区做了二十七年牧师,遇到这种机会就会说:魔鬼要干坏事总可以引证《圣经》。他一直忘不了一个先令就可以买十三只大牡蛎的日子。”这句话的内涵意味很强,因为欧洲人迷信牡蛎具有增强性欲的奇效。类似扬·斯蒂恩(Jan Steen)《女孩吃牡蛎》这类绘画,往往具有性道德讽刺的意味。一位年长的牧师成天惦记着吃便宜牡蛎,说出来显然不算什么好事。六便士可以购买半打牡蛎暗自享用,作为隐晦而自我卑污化的性器官象征,它和故事男主角与塔希提恋人爱塔的那位水手儿子屹立船头的自然健康形象,形成了强烈反差。
莫里斯·柯林(Maurice Cowling)指出,毛姆从刚开始写作就排斥基督教,是缘于“它对激情的憎恶、对永恒惩罚的信仰,还有灵魂问题上的唯我主义容易导致的残忍和自欺。” 在《人生的枷锁》里,菲利普想起保姆以前跟他讲过:“如果在小鸟尾巴上撒一撮盐,就能够轻易逮住它。可惜谁也没办法靠近小鸟。想必‘信念’也是这样:谁也没办法虔诚到足以靠近上帝。”他认为科学才是“烦恼的慰藉与治愈者”,而宗教的利他主义,尤其是清教式的利他主义,则是进化的障碍。人类需要自我实现与满足,否则生活没有任何价值。这些观点在《人生的枷锁》里已经有明确表示,所以他对一战时期宗教复兴不置可否,认为战争只能增加人们对宗教的不信任。他在《主教的围裙》《雨》《圣徒成长史》和《圣洁的天国》里对伦敦的教士阶层、南太平洋岛上的白人传教士、安达路西亚的天主教徒,都进行过辛辣的讽刺揭示。
相比之下,毛姆对佛教和印度教,其次是秩序分明的天主教,却要尊敬许多。他对佛教和印度教里的神秘主义成份尤其着迷,认为一个人只要能够理解它,就可以用来解决自身的需要和情感问题。他在《总结》里说:“经验表明,一种信仰的流行,无论它存在时间已经有多长,都无法保证自身是真理。”又说,“没有理由认为,如果你意识到自己的信仰缺乏佐证,就不应该继续信仰下去……直觉就已经足够”。在这个意义上,“神秘主义超越于佐证,其实它只需要内在的确信。它独立于种种信条……它是如此个人化的东西,所以能够适应满足所有的特质。”
柯林认为,毛姆小说里那些承载真理的人,可能是现实生活里容易被判定有道德缺陷的人。例如,《面纱》的中国通威丁顿,《偏僻的角落》里的尼柯尔斯和桑德斯,《刀锋》里的苏珊娜和苏菲。他那些具有神圣性的主角,也从来不是神职人员,并不比这些真理承载者优秀多少。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能够毫不妥协地抛弃自身幻想,认为神秘思想的力量胜过清教式的信仰。他们都能感觉到一种内在的精神召唤,愿意奔波求索,超越现代城市冰冷的物质性。这些人的理想代表,当然是《刀锋》的男主角拉里。他经历过各种迷惘,尝试过各种生活模式,目睹过各种悲惨不幸,求助于不同宗教和哲学,最终在印度瑜珈禅师指点下进入深山静修,完成了精神顿悟,再以“大隐居闹市”的方式回归纽约。
[英]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 张和龙 / 上海译文出版社
在拉里的实践过程中,印度教与基督教的效果形成了截然反差:他在基督教领域的用功和虔诚,最终只能让他感觉,自己与真正的信仰隔着“一层香烟纸”的厚度,而印度教则告诉他:“能够被人理解的神不算是神。谁能够用言词解释至高无限呢”。通过神秘主义的体验,拉里终于获得了灵魂的彻悟与宁静。
与其说毛姆在《刀锋》里提供了一条明确的救赎之路,还不如说他通过这位既像圣徒那样通透而无私、又能够自然表达七情六欲的主角,呈现了他对东方传统为科技昌明却精神衰朽的西方提供救赎的向往。毛姆本人对印度哲学其实不甚了了。他对印度哲学的系统了解,主要来自衣修伍德和他崇敬的斯瓦米·普拉哈瓦南达(Swami Prabhavananda)。1941年,毛姆到好莱坞与30年代末开始就专心研习吠陀经的三位作家衣修伍德、赫德和赫胥黎见面,探讨过一些印度哲学与和平主义的问题,并且开始酝酿出《刀锋》的相关题材。拉里反省战争时的和平主义思想,还有他对印度吠陀传统的研习,就是以衣修伍德为原型。
柯林说,毛姆讨厌犹太-基督教传统里那位无趣、不宽容、不断要求信徒们夸赞和崇拜、“没有绅士风度”的上帝。他对佛教和印度教的推崇,更多是为了抵消这位西方上帝的影响。他以诚恳态度向西方读者推广介绍东方宗教的同时,也提出一些批评看法。例如,阿特曼和梵天的观念,虽然比“个体灵魂”的说法更容易让人信服,但只是在“取悦于人的幻想”。印度教推崇的不朽,既让人感到深刻吸引,又让人无法完全认同,就像是“房产代理登在报纸上的广告”。
显然,老毛姆典型的刻薄多疑,即使在他真心推崇的事情上,还是会忍不住冒出头来。
一场人性的探秘
体味毛姆多面人生
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上一篇: 直播间里的新东方是怎么开挂的?
- 下一篇: 自我定位从哪几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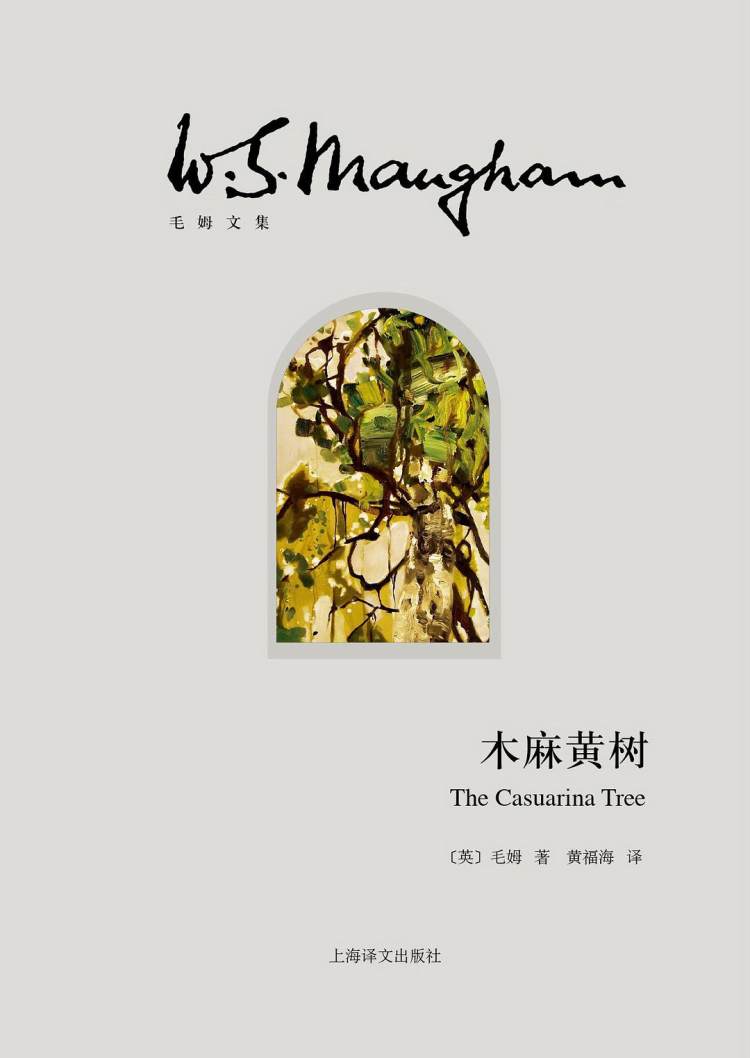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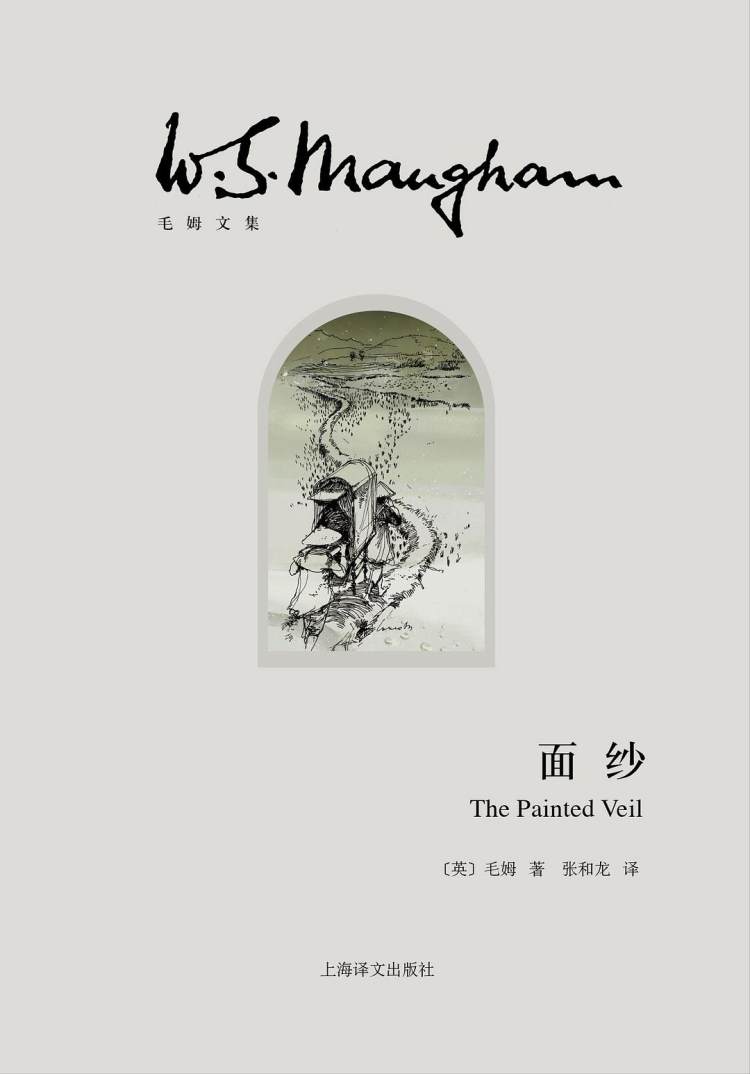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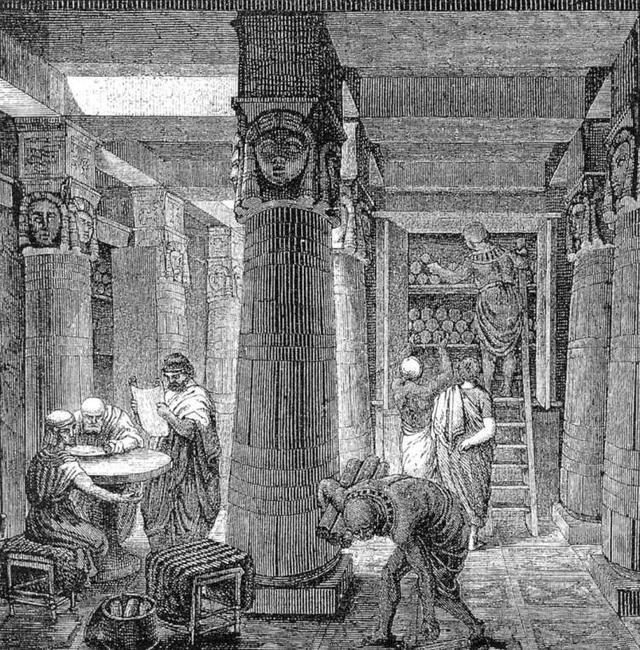

最新留言
说:写得非常好!
2020-10-28 11:1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