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侯乙编钟(部分),战国。曾侯乙编钟上刻有关于记事、标音、律名关系的错金铭文2828字,加上钟架横梁、编悬配件上的铭文、磬铭文、磬盒铭文,总字数3775字。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最常见也最常使用的,无疑就是汉字了。然而,早在100多年前,汉字却险些遭遇被“废除”的厄运。
熟悉清末民初历史的人都知道,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华民族处在内忧外患的变革时期,有识之士开始反思“落后”的根本原因。他们意识到,想要进步必须进行改革,可是该做什么、如何去做,却没有人能完全说明白。
有学者认为,民族之所以在世界发展进程中处于劣势,归根结底是因为整体思想的落后,而文字又是思想的灵魂,所以要想普及教育、提高国民整体素质、走向富强之路,就必须从文字开始改革。
于是,文化界掀起了两个改革运动,分别是肇始于晚清的“国语运动”和五四新文化时期兴起的“白话文运动”。前者是让人们直接放弃汉字,学习拉丁字母,后者倡导人们不再使用文言文。
在近代国语运动中,钱玄同始终是一名较为活跃的人物。/电视剧《觉醒年代》
如今看来,“废除汉字”的确有些令人匪夷所思——假如将汉字全部用更为简单方便的拉丁字母替代(将“的”写成“d”,将“子”写成“z”),我们现在的生活,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一切因果都是有迹可循的,汉字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延续了几千年,并沿用到今天,必然也是“历史的选择”。凭着“后见之明”的论调,不少人仍断然将“废除汉字”看作当时文化改革的激进行为,尽管在当时,汉字“维护论”也被简单地看作“顽固守旧”。
当然,这两种论调都是略显偏执的,但大家的目标却是一致的:找到能够适配民族的语言与文字。
为什么要“废除汉字”?
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里抛出了“废除汉字”的主张。/电视剧《觉醒年代》
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里抛出了“废除汉字”的主张,而这次运动的主要人物,像蔡元培、鲁迅、周作人、胡适、瞿秋白等人,都在语言观上支持“废除汉字”。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全之分析,如果忽视时代背景,仅从“废除”目标进行推导,这一主张难免会显得幼稚而莽撞,然而这背后,却隐藏着比口号本身远为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
事实上,“废除汉字”的实践,并不始于钱玄同,而是一股自晚清就开始了的文化运动。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为了在民间传播《圣经》,于是在厦门、汕头一带,推广一种用罗马文字拼写的当地方言,称为“Romonized Chinese”,这种文字不仅简单易学,还能直接拼读方言,甚至流传极广,成为最早取代汉字的“新文字”。
晚清时期,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播《圣经》教义,阴差阳错地推动了汉语语音学的发展。/图源网络
在张全之看来,这种拼写方式给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很大启发。于是在内忧外患的逼迫下,改革汉字、提倡白话之风,才得以在晚清逐渐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
1892年,福建同安人卢戆章出版了《一目了然初阶》,在书中,他仿照拉丁字母创造了“中国切音新字”。1894年,吴稚晖因为每天吃腻了豆芽,但是看到豆芽长得很像字典上的注音符号,便按《康熙字典》上的读音,创作了一套拼音字母,谐称之为“豆芽字”。
《康熙字典》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知识分子出于教化民众、开启民智的目的,于是开始忙于创制新式拼音文字,更有梁启超、裘廷梁、陈独秀等人不遗余力地提倡白话,将白话作为“教育民众的利器”。这两个运动构成了晚清语言、文字变革的主潮。
对汉字实行关键性打击的,是晚清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诉求世界大同,主张消弭国家、民族和人我之界。而要实现世界大同,就要先统一文字。这一思潮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迅速在知识分子中间蔓延,其中以推崇“世界语”最具代表性:“盖万国新语,实求世界和平之先导也。”万国新语是“Esperanto”一词的最初译名,又音译为“爱斯不难读”。
在提倡“废除汉字”的论调中,知识分子们依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克鲁泡特金(俄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家)的“互助论”,认为人类的语言文字也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并认定汉字同古代波斯的楔形文字一样,不仅复杂难学,且也不适合现代排版印刷,成为传播现代文明的一大障碍,应该彻底铲除。
语言学家黎锦熙。/图源网络
这样一来,汉字自然而然地就被纳入到了一个进化链中:汉字(象形文字)—西方文字—世界语。
积极推动汉字拼音化的语言学家黎锦熙就曾说:“汉字一天不解甲归田,古文便时时运动复辟,汉字一天站在普及的地位,白话文便时时要走向不普及的迷途。”
如今回看,钱玄同等人对汉字杀伐果断的主张显然是武断的,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或许是他们迫切启民智的无奈之举。旧封建礼教如铜墙铁壁一般禁锢着国人的思想,可能只有激进的做法才能更快地与旧时代告别。
不应忽视的“保守”论调
夏衍曾在《懒寻旧梦录》中提到,1932年,面对向他热情宣扬“汉字拉丁化”的瞿秋白,他虽内心不赞同,但“没有和他争论”。当时,左联负责人冯雪峰几次催夏衍在《文学月报》上发表文章,他也因不赞成“废除汉字”,“始终没有交卷”。
《懒寻旧梦录》,作者:夏衍。
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曾在其《中国语与中国文》一书中,对汉字做出过一些相当感性而知名的评价:“汉字是真正的中国精神创造力的产品……使人能发生无穷的想象,不像西洋文字那样质实无趣。”在他看来,废弃汉字是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自戕。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张世禄在继承高本汉观点的基础上,做了更为扎实的论证,并发表了《中国新文字问题》《汉字拉丁化批判》《汉字简化运动》等文章。他明确反对西方近代语言学的“进化论”,认为民族语言并无高下优劣之别,只是顺应民族历史的演化而造就出了各种语言特性。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张世禄在继承高本汉观点的基础上,做了更为扎实的论证,并发表了《中国新文字问题》《汉字拉丁化批判》《汉字简化运动》等文章。/图源网络
由此可见,在“废除汉字”的呼声最高涨的时候,也不乏有识之士与“汉字革命”阵营持不同的意见。然而,以科学面目示人的“文字进化论”,总是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将“文化保守派”远远地甩在身后。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湛晓白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发现,晚清之后“趋新思潮”占据主导,文化的“激进取向”往往比“文化民族取向”更能吸引眼光和打动人心,这就决定了“废除汉字”在舆论上取得优势地位,而从文化认同视角“维护汉字”的言论,屡屡遭遇嘲讽。
清末,以章太炎为首的国粹派学者,主张自古迄今汉语与汉字之间不可割裂的独特文化联系。这种联系,正是被“汉字革命”阵营所忽视的。那些对“世界语”的批驳,也奠定了维护汉字的文化民族主义论述的基调,其间蕴含着值得今人借鉴的思想价值。
史学家钱穆曾相继发表《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古代学术和古代文化》等长文,从民族主义的视角,对汉字做了最为虔诚的辩护。/图源网络
史学家钱穆曾相继发表《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古代学术和古代文化》等长文,从民族主义的视角,对汉字做了最为虔诚的辩护。他历数汉字优越于拼音文字的地方,指出能“兼具形声之长”是汉字最大的优点。
钱穆还认为,汉字具有“以旧话而构新名,语字不增,义蕴日富”的特点,表现为能以千余常用字构造上万之新鲜组合词,不仅简明远超乎“谐声文字”,且在翻译西方现代科学、哲学术语的时候,也毫无“困难扞格”。他因此断定:“此则中国文化绵历之久,镕凝之广,所以其有赖于文字者为独深也。”
抗战时期,文化民族主义思潮高涨,在这样的契机下,强化汉字文化认同和大一统功能的言论,才得以获得“同情”,汉字的文化价值,重新为“维护汉字论”提供了支撑。
中国的语言,
天然与汉字适配
关于“汉字拉丁化”的论调,总的来说就是两点:一是汉字结构繁杂,不便认识和记忆;二是汉字为一字一音,必须与文言文为伍。现代汉语中大量出现的复音词、组合词,成了推行拼音文字的充分条件。
相较于拼音文字来说,结构复杂的汉字更加难学难记。/图源网络
然而,张世禄对这一逻辑相当质疑。他曾指出,汉字表音功能差,确实“不足以为实际语言的记录”,但“这种艰深的汉字居然会数千年来沿用而未曾变更,是否在民族社会的实情上还有存在的需要?又是否和各处方言分布的情形,另有相适合的因素?”。
沿着此思路,张世禄对汉语作出了重新探讨。在他看来,汉语的性质和方言林立,决定了记录和书写汉语的文字,必然也发展出了“形声兼具”而又以表意见长的特性,这是语言与文字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自然适配关系。因此,不能将维护汉字归咎为“顽固保守”,“实在是由于中国的语言,天然和这种文字适合的缘故”。
那么,历史上适配的汉语与汉字,到了近代之后是否因汉语性质的改变而难以共存?
1918年,鲁迅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张世禄认为,近代“白话文运动”的开展,促使了现代汉语复音词进一步增多(由两个或以上音节构成的词,例如:学习、徘徊、再见)。“这是客观事实,但这并未使汉语从根本上转变为复音词的变形语,所以说国语为单音缀语的说法至今还是可以成立的。”
据此,赵元任曾写下一篇“同音不同字”的《施氏食狮史》,全文只有一个读音“shi”。如果把它翻译成拉丁文,通篇的“s”,恐怕就没有人看得懂了。这篇96字的“奇文”,惊动了民国文学界,阻止了汉字被废的命运。
赵元任《施氏食狮史》汉语拼音版。
除此之外,赵元任还写过《季姬击鸡记》《易姨医胰》《熙戏犀》等,一次次证明了汉字的博大。“用同一个读音创作一篇文章,且语言通畅、意思明了,恐怕只有汉字才能做到。”在他看来,采纳何种形式的民族文字,根本上取决于民族语言的特点,现代汉语的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汉语与方块汉字的适配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也在北京成立。为了使汉字便于使用,吴玉章组织领导了简化汉字的工作。1964年《简化字总表》发表,收字2274个,随后向全国推广。
1978年,上海。火车的标志上同时标有汉字和拼音。 /图·视觉中国
在接下来几十年的探索里,人们发现中国并不适合用拼音文字,因为汉语中有太多的同音字和同音词(例如:“攻击”和“公鸡”),而这些同音词只能用汉字来区分。
因此,表音的拼音文字也就只能作为汉字的辅助音标,并不能取代汉字的书写。就这样,文字演化,最终还是呈现了工具性能层面的“简易化”和语义稳定“明晰化”相结合的趋向。
在文化全球化已成滚滚洪流且利弊共生的当下,如何建构既面向现代,又保全充分主体性的民族文化,仍是我们需要面对的宏大现实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近代中国汉字存废论争所展现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冲突,及其昭示的历史方向,或许可以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一些借鉴和反思。
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上一篇: 不会化的雪糕,你敢吃吗?
- 下一篇: 今天12点,听周董了吗?/ 五成00后“一定会买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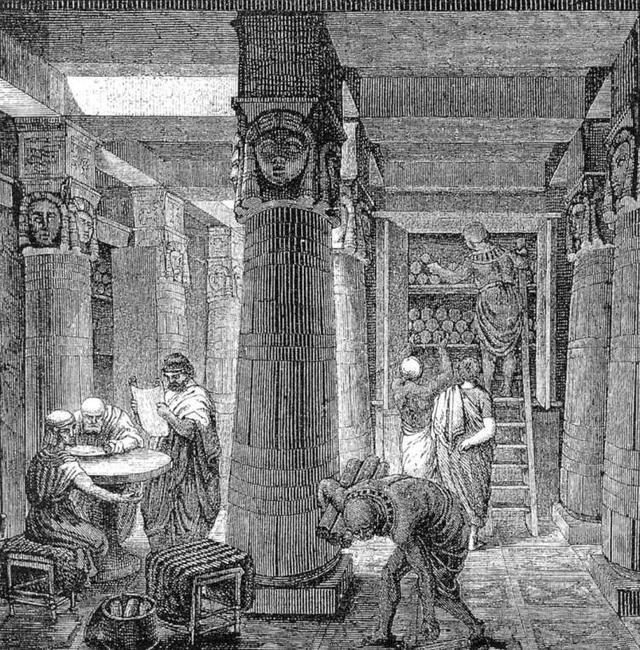

最新留言
说:写得非常好!
2020-10-28 11:15:56